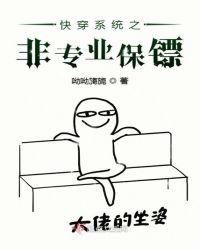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沉疴 > 3三念错声(第1页)
3三念错声(第1页)
当天晚上,宋持怀久违地做了噩梦。
梦里是一间破败的柴屋和一个灰黑的冰桶,他被人捏着后颈强迫性地灌在冷水里,四处漏风的木屋摇摇作响,腊月寒风刀子一样割在身上。少年青涩生嫩的脸上被划开一道道破口,他低着声想要求饶,嗓子却早已烧坏,咿呀地发不出声音。
他想逃,却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拳踢脚打,少年单薄的身板并不足以应付成年大汉的单方面殴打,于是他断了骨头、手脚难动,施暴者们却以他狼狈的样子为乐,好不容易痛晕过去,一盆盆掺着冰渣的冷水倒在身上,他被迫醒来,又是一轮新的折磨。
冷,痛。
宋持怀身上无声浸了一层冷汗。
无边的冰水将他包围,寸寸攫夺他鼻腔里所有空气。
眼前最后一丝透下水里的光也将要消失,宋持怀绝望地在水下睁着眼,亲眼见证自己是如何彻底被黑暗吞没。
就在最后一丝明光将要消失的时候——
“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将他惊醒,宋持怀瞬间睁眼,他看了好一会儿床帘才渐渐回过神来,不住揉了揉太阳穴,向着门外问询的声音沙哑疲惫:“谁?”
“是我。”
魏云深的声音带着不确定性,“我在外面听到了点声音……你没事吧?”
他本来只是象征性问一下,毕竟已经听到了宋持怀的声音,人没死就能算没事。然而这回却久久没听到回应,魏云深不由真的担心起来,正踌躇要不要进去看看,里面突然传来一阵窸窣响声,没等他反应过来,宋持怀的卧房已被打开。
素白人影倚在门框上,还带着几分倦意:“有事?”
他起得仓促,外衫套得匆忙,头发还没来得及束,衣襟处也不大平整,却不让人觉得邋遢,反而更添一种凌乱的美感。
一小片光滑的锁骨显露出来,细腻分明的肌理往下延伸到半遮半掩的衣襟里处,魏云深咽了口口水,忽然心虚地移开目光,发声也变得艰难:“我,我就是路过……”
不对啊,他慌什么,他们不都是男人吗?
男人之间不小心看个锁骨而已,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吗?
魏云深说服自己,镇定地把视线挪了回去,他说话与神态都透着关心,脸上却飘了一团可疑的红色:“你没事吧?”
“没事。”
缓了一会儿,宋持怀才从刚才噩梦的心悸里恢复过来,他抬手按了按因刚睡醒而氤氲发红的眼角,反问,“怎么起这么早?”
魏云深看得愣了一下,脸又红了起来,他转过头,深深吸了口气:“睡不着就起来了,想着天气好就到处逛逛,谁知道刚到这边就听到里面……”
他还是有点在意,十五六岁正是最憋不住话的时候,魏云深随便跟宋持怀多说了两句就没忍住继续问,“你刚才……”
“只是做了噩梦。”宋持怀神色平静,不动声色地换了话题,“起这么早,饿了没有?”
“啊?”
魏云深一下没反应过来饿没饿跟起得早不早有什么必然联系,他果然被宋持怀带过去,一想还真有点饿了,于是顺势接茬:“是有点,这里什么时候吃早饭?”
“天极宫内没有吃早饭的惯例。”宋持怀轻轻摇头,看着面前的少年因自己的话微微瞪大了眼,心里觉得好笑,于是又道,“修行之人大多辟谷,五谷杂粮易添浊气,于修行不利,你若想要更上一层,也该要早点习惯才是。”
“……”
所以宋持怀问他饿不饿是为了什么?不是邀请他吃早饭的吗?难不成只是随便问问?
魏云深这才后知后觉想起以前似乎确实在话本子里看到过修仙人不用吃饭,瞬间垮下脸,神色忧虑:“一点都不吃吗?我还没学会辟谷呢。”
他向来藏不住什么心事,忡忡忧心几乎写在了脸上,宋持怀被他皱成一团的脸看得心情好了不少,忽然低眉道:“山下有些过路摊贩,卖什么的都有,你若实在饿得受不住了,可以跑下去看看。”
“你要我一个人跑着下去?”
魏云深不可置信地立马瞪大了眼,他想起昨日上山差点累死的那两匹马,至今心有余悸,“怕是我饿死在路上都还没见着山脚吧?”
这话不算夸张,上峰的小道蜿蜒曲折,攀顶之路峭壁横生,平日里天极宫门人仗着有修为傍身才得以进退自如,要他一个凡人为了一顿饭跑上跑下,倒不如直接叫他从鸦影居后的石崖上跳下去,起码死得干脆痛快,不用白白受爬山的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