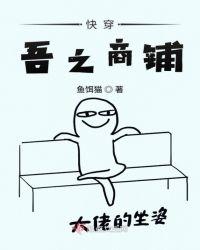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当怪物们开始恋爱 > 第173章(第1页)
第173章(第1页)
“小憩那十来分钟我就开始做梦,梦见学校,学校还是我们现在的学校,我就在教室里听课。我醒来后还对梦里的事记得很清楚,大夏天教室又闷又热,我就看着讲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冷,外面也黑下去,像是到了晚上。我一转头想和旁边的人说话,结果一回头就是汪泉,四周的人、连老师都是他,不约而同都看着我。”
“他当着我的面用削尖的铅笔戳进自己的脖子,鲜血噗嗤往外飙,我的脸上、衣服上都是他的血——”高骥回忆这一幕还是觉得不适,自己伸手摸着脖子,好一会儿鸡皮疙瘩才下去,“他又从脖子里将笔拔出……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他向我走来……醒来后我就知道我要死了,就跟之前那些人一样。”
他说完,重新低下头,身上除了羽绒服还裹着被子,声音虚弱重复道:“我真的……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想起之前停驻在面前的双脚,运动鞋上血迹斑斑,裸露在外的小腿上尸斑浮现,而汪泉的声音就在头顶:“高骥,这里好冷。”
寒冷在冰冻他的理智,人在极度恐惧之下根本无法思考。
“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变成鬼,只是自己不知道,电影里不也有这样的情节吗?”高骥苦笑,“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害怕光线,恐惧阳光,好似我躲进黑暗里汪泉也能看不见我一样,掩耳盗铃。”
单绪给他续上热水:“所以你就一个人?没想过寻求别人的帮助?”
“哥,这要怎么寻求帮助?之前死的人没试过吗?闹得全校都知道,警察进进出出,有用吗?”高骥神经质地抖着腿,“而且,虽然我这人私生活不怎么样,但是道德上……我不想再让别人卷进来了。单哥,我知道你喜欢钱,你放心,好歹朋友一场,我这段时间已经拟好遗嘱了,等我去了……”
说到动情处,高骥忍不住埋头哭起来:“哥——我现在要是死了,我都还没跟人上过床!你说我多惨,都快要跟男人脱裤子上床了,结果遇上这事。”
单绪能平静的听完,但身边的小男鬼猝然一个起身:“单绪!”
声音比高骥的鬼哭狼嚎差不多。
“他刚刚说什么?!”周子燃绕到高骥旁边,因为对方低着头,他还蹲在地上,试图去看他的长相,但是高骥将脸埋在臂弯里,只露出一头短发和下巴。
周子燃不是怀疑自己看花眼了,就是怀疑自己刚才听错了,回到单绪身边大叫:“他是女生?”
单绪知道他在惊讶什么,小可怜鬼的,可能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一个活同性恋。
“别哭了。”单绪被他嚎得心烦意乱,将桌上的抽纸往他那推,“我只收活人钱。”
高骥哽咽不止,小男鬼拽着旁边人的手——单绪扫了一眼,觉得这鬼有些蹬鼻子上脸,现在时不时就抓手握手的,占便宜的小动作已经懒得掩饰了。
“单绪,这人真的是女生?”
高骥扯了几张纸擤鼻涕,红着眼睛:“单哥,这还是你第一次拒绝金钱的诱惑。”
“现在了,你脑子就想的这些?”单绪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他,“那个男人你都没仔细想过吗?”
“想啊,怎么不想了,就是这些天汪泉时不时就出现,导致我想他也硬不起来。”
“他是男的?!”单绪被这声鬼叫吵得揉了揉耳朵,斜眼看见小男鬼大退一步,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高骥看。
单绪:“白痴。”
一句话把人跟鬼都骂了。
他看见自己的手臂又被鬼缠住,真被学生鬼听见成年人劲爆的八卦,亢奋地拽住单绪的手就狂摇:“单绪,他是男的!他跟男人上床!你听见没有!”
你还晚上偷摸男人胸呢,单绪觉得小男鬼的行为更过火,可当事鬼没有这个意识。
单绪随便小男鬼怎么兴奋,都当作没听见也不回答,只专心对着高骥再骂了句:“我看你脑子装的都是屁股跟雕,现在都快死了想的也是这档子事。”
他双手搁在桌上,口吻严肃:“你就没想过那录像带是他故意给你看的?就像汪泉搬走前故意给我留下了一卷录像带,都在找替死鬼,结果事情过去这么久,你想到罪魁祸首只是遗憾没能做成爱?”
好直白哦。
什么屁股跟雕,什么做成爱,这让周子燃听得面赤耳红,松开手小声阻止:“单绪,你说话别这么直接。”
高骥哭声一顿,泪汪汪看着对面的人:“啊?”
他好似没回过神,想了想:“不会吧单哥,他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人。”
“……”单绪的手开始痒,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白痴,“你那天晚上醒过来发现录像带放着,已知地点在他家,当时只有你跟他两个人,你失去意识,请问,这录像带是谁放的?”
高骥嘴唇哆嗦个不停,一副备受打击的模样,眼泪哗啦啦往下掉:“这个——”
他哭腔比刚才还重,高骥一拳头打在桌上,震得叽里呱啦说话的周子燃都闭上嘴。
“所以他找我只是为了找替死鬼,那这么多天的联系、见面算什么!”高骥周身萦绕着被负心人背叛的绝望,“那他约我去他家,不是戳破关系,也不是做‖爱,更不是喜欢我,他就是要我这条命!”
我的天。
周子燃抿着嘴,靠在单绪身上小声同情:“他好可怜。”
单绪额头抽痛,拳头攥紧,咬肌也在高骥一声声的嘶吼中用力咬紧:“高骥,你没救了。”
死到临头想的还是喜不喜欢,蠢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