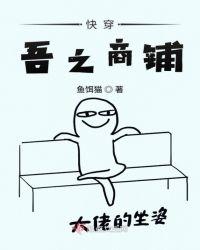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HP]重生之汤姆观察日记 > 第 154 章(第3页)
第 154 章(第3页)
她在等落雪,等天意。
今早多丽斯才醒来,床榻上的清冷味道还有留存,汤姆才走没多久。
今年暑假在新西兰Queenstown滑雪,雪山上,目光所在都是晶莹白雪,多丽斯眼中只有他一人。
心有所感的她就对汤姆说,他身上有这种清冷似雪的味道,不是香水味道,是一种感觉。
他轻笑了一声,只当是性格或气质之类的。
不是的,她当时只是笑笑没反驳。
如果照他信上的说法,是他们灵魂的相互熟悉,而曾经散魂的她,也正是自1953年和汤姆的再次相遇,才有了这个感知。
他碎过的灵魂,是冷的,是残杀的人血一点点降低人性的温暖,这是清冷的缘由。
混淆咒加上绿树枝叶的掩饰,树冠上躺着的多丽斯,没有惊动树下往来人群的一丝关注。
她只是半睁着眼睛望向手指上的婚戒,莹莹绿蛇头上的悬浮血液始终保持着米粒般的大小,这代表汤姆仍然在戈德里克山谷的那片墓地。
多么卑鄙的一个人。
明明白白地怀疑她,轻视她。
多丽斯自嘲笑了一声。
就算他不是她道侣,但她最初的契机就是她爱他,情感一直折磨着她,偏偏他从来不说一句‘他爱她’。
果然,爱得多的,先弯腰。
她要根据他的态度,来做最后的抉择。
夜色降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没有一点雪花的飘落痕迹,哪怕是微小雪粒。
循着教堂后面的窄门,多丽斯来到了这片墓地。
眨眼间的黑眸加深,多丽斯抬头看去,一排排墓碑伫立在浅蓝色银毯上,刻满古老巫师家族的姓氏。
记忆里的熟悉道路,很多年来,每年12月31日的上午,他们都会来到这个墓地,这里埋藏着梅洛普·冈特。
左手紧紧握着常年当作发簪的鸣凤枪,比起十多寸长的短小魔杖,多丽斯依旧习惯一丈枪,晨间的锻炼,她数年如一日的武器仍旧是长枪。
清冷味道的终端,是墓碑前沉默的黑红巫师袍。
不看见他的时候,她恨不得揍他一顿,混蛋,骨子里的悲观主义者,尽是逮着她一个人欺负。
现在看见了他背影,多丽斯就有点无所适从,眨了眨发酸的眼睛,她手中的发簪还没有变大成长枪的模样。
她还不想亲手杀了他。
他们的父母都死了,如果汤姆不认和她的这段婚姻,不认这个家。
厌恶他的父亲,早死的母亲,除了霍格沃茨学校,还称得上家的一点温暖的认同,只有梅洛普长眠的这里。
他没有家了。
该死的共情。
看了许久,多丽斯叹了一口气,一步步靠近微风摇动的黑色衣袍,她才跪坐在他身边,就听到汤姆冰冷的声音,
“你不该来的,风暝,你以后肯定会追悔莫及。”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轻视我的感情,我原打算是来取你性命,结束我们漫长的人生。”
他拿魔杖的那只手是右手,轻声的说话回荡他冰冷的耳畔。
汤姆垂眸看去,她的手,和他一样冷。
这才是残酷的真相,不是道侣。
他知道,她就在戈德里克山谷,待了近12小时。
那天嘴唇上的感知只是一个错觉,但今天的肌肤接触,戛然而止的28年暖意,就像是一种迷幻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