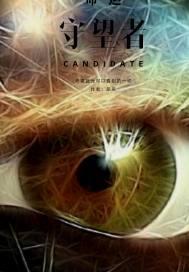墨澜小说>秦皇汉武唐童现代留学日常 > 90100(第33页)
90100(第33页)
临行前,上卿张苍来与他们聊过贡品的事。那时诸公子还怀有忧心,担心自己的封国贫瘠,拿不出像样的贡品,像当初只能进上滤酒茅草的楚国一样丢脸。
而且是写到史书上一丢就是八百年的脸。
又有人担心贡品太贵重,会耗损国力。
张苍却告诉他们,大秦一统天下,事事都是新立,诸侯上贡也是一样。天子会考虑到诸侯国的难处,西域出产的美玉固然会列为贡品,却不会强求太多。
而诸侯国的农业出产和特色工艺才是大头。在上贡的同时,允许他们享有一定的免税额度,与贡品一起运到咸阳。
嬴高的思路被打开了。他明白了,如果有贡品的名义,只要不是楚国滤酒的茅草那种贡品,那必然会一售而空啊!
只要是真正的好东西,哪怕超过了免税的额度,运出去卖都不会吃亏。所以他来了之后四处巡访,也四处吃吃喝喝,就打算定下贡品好去说服父亲。
现在看起来,葡萄干和葡萄酒就是最合适的了。
蒙立又在名单里添了杏干,这边气候使然,果子的甜度都非常高,可惜新鲜果子实在来不及运出去卖,只能挑这些加工过的干果了。
有了初步思路,嬴高踌躇满志,只待大干一场。他嘱咐蒙立:“回王宫后提醒寡人给兄弟们写信,彼此相邻,正应互通有无。”
他的兄弟之一,公子将闾封在了疏勒,为疏勒王。
将闾有两个同母兄弟,封在了乌孙。乌孙是西域大国,物产丰饶,所以朝廷分割成了好几个国家,将闾的两个同母弟分到其中两个小国。将闾就不一样了,他独享疏勒。
主要这地方除了少数能种粮食的地方之外就是草原牧场。放牧固然不穷,但不太稳定。更重要的是,看起来地方很大,实际上还有大片的沙漠,根本就是废地。
不过将闾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草场,他是个闲不住的。
就在嬴高带着人巡视他的良田牧场和果林时,将闾也看过了他的没什么新鲜花样的草场和田地。嬴高还没有结束巡视的时候,将闾带着人来到了沙漠。
他的国相出自王氏,是丞相王绾家的子弟,现在都城替他管理国事,着重登记户籍和建立毛纺厂的事情。跟着他吃风沙的是率队护卫他安全的国尉,同样出自名门冯氏,名长。
冯氏家风不错,出色的子弟才兼文武,可出将入相。但冯长资质有限,并不长于文事,所以只负责武事。他和将闾一样,用特制的纱巾将头脸裹住,戴着手套,抓着一把麦草顺着风向使劲拍打,把碎烂的麦草扬弃后,握着合格的长麦草蹲身,码放在沙土上的正方形边线上。
这是隶臣画好的,冯长觉得画线的活轻松,他想干那个,让隶臣码草就是了。但是大王也在拍草码草,他只好叹口气,继续干活。他这个资质在冯氏不出众,在秦国不可能出头的,顶天了做个县令。有这个机会跟公子到封国做了国尉,他很知足,也很努力要做好。
就算公子,哦现在得叫大王了,就算大王带他不打仗而是种草,他也要做好。
将闾已经码好一格了,拿起铁锹沿着边线使劲踩压下去,麦草的中端压在线上,受了这力道,顿时陷入沙中,从中间翻折上来。
将闾回首望去,沙面上已经绵延布满了这样整齐规整的草方格,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招呼冯长:“国尉歇歇吧。”
冯长赶紧跟住他,走到边上不妨碍隶臣干活。君臣两人毫无形象地一屁股坐在草垫上,解开纱巾,大口饮水。
将闾灌水灌得过瘾了,哈了口气,转头问冯长:“国尉心里莫不是在怨孤吧?”
冯长吓了一跳,正要辩解,将闾笑道:“孤就国前去查阅过宫里的藏书,才知道来疏勒别事尽可不管,治沙才是孤必须做的。”
他指了指这片沙漠,脸色郑重起来:“每年风起,草场也会受到沙暴影响,更不用说这沙子还会‘吃’掉草场,让寡人的封国变得贫瘠无用。”
虽说推恩令下渐次分割,但那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况且他的子孙在身毒还会有封国,初去时也得疏勒这里给予支持才行。
要是到孙辈时草场缩小,再分给几个儿子,哪还有余钱啊。
而且父亲专门问过他治理疏勒的思路,他提到了治沙,能看见父亲满意的点头。
父亲一向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情绪和态度,这样明显的表态,显然在父亲心中,治沙也是件大事。说不定让他来疏勒,就是让他治沙来的。
将闾自然把这当作头等大事,能给他积攒财富的毛纺厂都不去关注,亲自带人来了。
不过他没有对冯长细说,而是道:“治沙不但能保草场,将来在这里修路也方便,免得路总被沙埋了。草格固沙五年一补,我不亲自来做,旁人哪里能上心。”
冯长憨憨地点头,反正大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大王早有成算,接下来他还要带人在草方格里种胡杨,种沙蒿,种梭梭。梭梭种成后,就可以用梭梭做宿主,种植肉苁蓉了。
将闾摸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了看抄下来的肉苁蓉药效。
肾阳虚衰、精血亏损、腰膝冷痛、耳鸣目花、带浊、尿频、崩漏……
咳咳,他就打算用这个做贡品来着。将闾目光落在前两个病症上,咧嘴笑了一下又赶紧闭上。
不是他说,别的都不用看,就冲这两个对症的药用价值,他的肉苁蓉肯定能大卖,他还不懂他们男人么,没病也会买回去煮粥喝了补身体的。野生的挖多了来不及长,迟早挖绝种,他抄到这个的时候就决定要人工种植了。
所以他可看重这草方格固沙的作用了,亲自来做就是表明态度。将闾很清楚,他来到西域为王,关中能给他的支持不多,西域这些胡人是必须要用的。
但是胡人与秦人两相疑虑,磨合需要很长时间,他也不能一味的以刑杀震慑。
在咸阳学习时,他在帝师韩非子那里学过统御之道,但是他深深觉得自己做不来父亲那样。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对治沙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