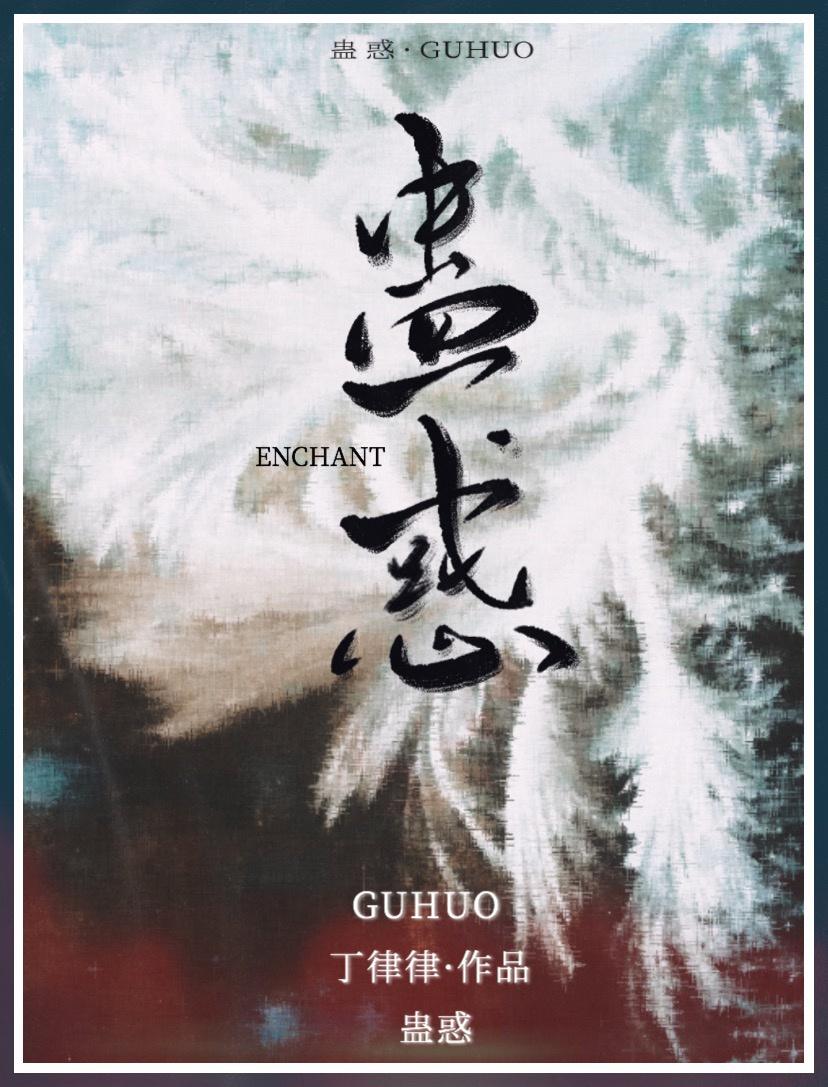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何以安山河 > 第492章(第1页)
第492章(第1页)
肚子咕咕叫,他异常的矮小瘦弱,两只冻疮累累的手死死扣着冻硬了的麻绳,唯恐一个抓不牢再把柴火散失了,中午晚上全没饭吃,就早晨吃了一口冷汤,衣衫褴褛单薄,他也分不清自己是冻得全身疼,还是病得全身疼。
“爹,娘,儿子全身都疼,也不能怪婶娘打我,现在年头不好,谁家里多一张嘴,心理也不痛快。”
他伸出黑乎乎的袖子蹭了蹭眼睛,吸溜鼻子,晚上看,小奴仔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在冻得黑红的小脸上极不相称,自己安慰自己:“不能哭,哭了流眼泪,脸就被冻得更厉害了;要干净,不干净的孩子更不招人喜欢。”
他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苦中作乐:“爹,娘,你们虽然走了挺多年了,可我还记得,你们不是告诉儿子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吗?我是正月十五生的,以后还说不上能当官呢。”
烂鞋露出脚趾和脚跟,每走一步踩得雪壳咯吱咯吱响,真冷啊,他实在走不动了,愣神站在村口上,望向村里的方向,村里几排草房炊烟袅袅,估计是晚上临睡觉前正在烧炕,炕上会暖呼呼的。
他已经不记得热炕头的滋味了,叔叔婶娘带着几个堂哥堂姐是住在炕上的,他住在厨房里。
厨房也挺好的,上半夜灶坑里还有热乎气。
他知道今天只捡回来这一捆柴火,晚上肯定没有饭吃了,但是能凑合到厨房灶坑里的热乎气也挺值得期待的。
他喘着气,身上疼得厉害,尤其是关节和肚子里,想坐下歇歇,可背着柴火的时候不能坐,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他拖着干柴往回走,又困又累,脚下一个趔趄:“爹,娘,儿子不想当官,儿子能像小时候暖暖和和的有个家就行了。”
他说话带着哭腔,不知所云的乱说话,就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奴仔,加油,快到家了,不能在路上睡,睡着就起不来了,爹,娘,儿子就算是遭了这样的罪,也感激你们把我生出来,要不奴仔不知道人间是什么样子的呢。”
自己叽叽咕咕的说话,终于要到家里了,他不自觉站在家门口,发现柴门是大敞实开着的,有些奇怪:“咦,今天大黄狗怎么没出来接我呢?”
叔叔婶娘家能给他好脸色的,除了叔叔偶尔偷着塞给他点吃的,也就剩下大黄狗了。
他突然觉得这走回来的一路异常安静,要是平时他这么晚才捡完了柴火进村,村里的狗早就“汪汪汪”叫个不停了。
小奴仔站住了,试探性的压低了嗓子喊了狗子一声:“大黄儿?”
没有声音。
他看草屋里好像点着灯似的,不禁揉了揉眼睛,平时家里晚上肯定是不掌灯的,费灯油,好像有影子映在糊的窗户纸上影影绰绰,几条影子高壮极了,明显不是叔叔婶娘他们的身量。
他开始害怕,心怦怦乱跳,看来家里进了外人了,条件反射似的微微一曲膝盖,把柴火放在地上了,把两条细瘦的胳膊从绳子里退了出来,悄悄的往院里走了几步。
冬夜空气冷冽,雪沫子的味道里,好像还夹杂了不详的血腥气。
他凝神仔细看,在距离院门十来步远的地方,一片雪地上的殷红显示了血腥气的来源——大黄狗躺在那里,脑袋和脖子已经快要伶仃分家了,夜色中的鲜血殷开了一片,明晃晃的渗到了身下的雪地中。
大黄狗被杀了吗?村里家家养狗看守门户,谁都不会杀自己家狗的。
谁干的?狗死了,叔叔婶娘呢?
他手捂着胸口,开始一步步往后退,本能的察觉到了杀气和危险,应该快点逃离这里!
无论发生什么事了,全不是他能应付的,他又咬咬牙下了多大决心似的,万一叔叔和婶娘他们还活着呢?他应该去找村长和村里的亲戚,让他们来家里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