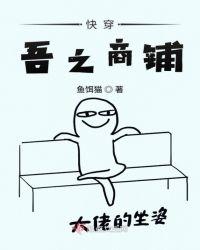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三国]你管这叫谋士? > 第 470 章 番外十3(第3页)
第 470 章 番外十3(第3页)
不对啊,就算她冤枉了同学,大不了就是来上个当众的赔礼道歉,甚至是多写几份检讨,何必给自己找个长达半年的苦差事?
现在可才是三四月里,薯蓣最快收获也得到八月之后啊!
孙鲁班只觉自己眼前一黑。
但她的脾性如何,早在她和乔桓的数次接触之中就被对方给摸了个清清楚楚。
乔桓怎么会看不出,这家伙要强得很。
上次,她能因为那句下次再分高下而选择那句“典韦打虎”的解释。
这次,她也能因为自己已经答应了乔桓而做出恪守诺言之事。
“母皇真是太厉害了,”乔桓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当年为了填饱并州子民肚腹的手段,居然在今日还能进行二次利用。”
“也难怪只有她才能结束这汉末乱世,成为天下之主呢。”
姜维听她嘀嘀咕咕,问道:“你在说什么?”
乔桓一本正经回道:“我在说,我们实在是运气太好的一辈了。建安年间的数年灾荒未曾波及到我们身上,再往前的光熹、中平年间的蝗灾也早已过去,不必经历当年将救命之望都寄托在薯蓣上的可怕境遇,也难怪书院要我们时刻牢记忆苦思甜。”
这种忆苦思甜的培训也并不只在这个课外种植薯蓣之事上。
孙鲁班毫不认输地在课余打理完了田垄间的杂草,本想去寻乔桓展示一二,却见对方并不在那片本该由她负责的田地中,就连一度被孙鲁班误认为是乔桓打手的司马昭也不在。
“……这又是什么情况?”
她寻人去打听了一番才知道,蔡邕这家伙讲课以诗经之中的无衣为代表讲到了战歌,又由战歌讲到了边塞诗。
那这其中便不得不提汉武帝所作的《天马歌》,和汉时《铙歌十八曲》之中的《战城南》。
前者还算好理解,便是汉武帝当年从那西域之地得到了一批汗血宝马,完成了外邦征服,自然在诗歌中透露出一番自豪的情绪。
但后者……却远不是乔桓这个年纪的人所能理解的东西。
她们至多是在诵读到“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的时候,直觉这并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打斗,而是一种战事悲烈。
可乔桓再怎么聪明,在她出生便已天下太平的情况下,她从来就没有机会真正见到交战的场面。
而有这种情况的也并不只有她一个。
蔡邕这人喜欢较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对于自己这个学年从头开讲的课程抱有很大期待,甚至希冀于将其在自己死后流传下来,变成乐平书院有人接管过去的课程,便干脆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带着这群上这门课程的弟子往塞外去走一趟。
只有亲自领略了关外风物(),才能真正明白边塞诗中的壮烈。
所以现在蔡邕带着这群学生抵达雁门关?()_[((),然后出关旅游去了。
“……”孙鲁班沉默了好半晌才问道:“之前到底是谁说蔡伯喈这个课很没意思,又不点名,轻松过头,迟早养出一帮闲人的?”
现在这帮闲人倒是在有专人确保他们的薯蓣田地正常生长的情况下,全跑去塞外游历去了。
更让孙鲁班觉得有点牙痒痒的是,陛下因蔡伯喈的身体状态经不得颠簸,也为了防止这些学生出意外,先是将一批以橡胶制作了轮胎外套的马车调拨到了并州,又令身在白道川驻守的吕布担任起了这趟出行的保护人。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出什么问题,那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于是这列出行的队伍原本只是打算走到塞外百里,见一见这阴山以北景象便回返,却最后在行离雁门关前决定,他们直接往赛音山达去。
吕布反正是不会拒绝这个建议的。
看看吧,这个队伍里有蔡邕和他的众弟子,那么以蔡邕这等务实求真的教学宗旨,在看到赛音山达的那块勒石记功碑铭,是不是得再给人讲解讲解彼时的事迹?
虽说以蔡邕的脾性,他可能讲一半就要往陛下的书法造诣上去扯了,但吕布怎么想都觉得,他是血赚不亏的。
再者说来,这队伍里还有乔淮序这位有意思的小殿下。
吕布还能趁机和她商讨一二,有些情节是不是可以写得再带劲一点。
“说起来,那小子为什么一直在看你?”在察觉危险上远比旁人要敏锐的吕布当即留意到了司马昭的不寻常。
乔桓无奈地摇了摇头,“没办法,我继承了母亲的英明才智,当然要多受到一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