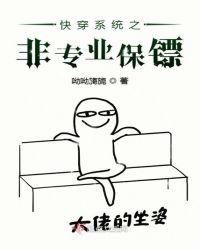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正当关係 > 李泽靖 03(第1页)
李泽靖 03(第1页)
我小的时候,我母亲总会说:「阿靖,你长得很漂亮,像你爸年轻的时候。」
我总会气鼓鼓的反驳:「妈妈,漂亮是形容女孩子的,我才不漂亮呢。」
母亲还是笑盈盈的,把我搂在怀里。
「男孩子也可以漂亮,漂亮不只是脸蛋好看,也是一种特别的气质。清清爽爽,就像停在树梢上的一阵清风。每一隻鸟都想留住那阵风,但风怎么会单独属于谁呢?风一定要流动,一定要吹拂,所以它才成为风。」
我眨巴眨巴眼睛,不能明白她的意思。
「风是被欣赏的,你要把它收藏起来,它就不再漂亮了。」她说。
时至今日,我才算有点明白母亲的意思。
但是对于我的漂亮而言,它只是算一种无用的招惹——招惹是非,招惹议论,招惹不该招惹的人。
第一次招来灾难是在12岁。
我刚转学,勉强塞进初中的一个班级做插班生。那个时候我刚刚认全26个英文字母,难以跟上英文课,老师安排一位女同学坐我同桌,帮我补习。
我记得她也是李姓,叫做李芳年,当了好几门学科的班长,人很大方,话也很多。她用课馀时间帮我补习,我对她心有感激,一直很听她的安排,但竟没有察觉她逐渐把我当成「所有物」。
一开始她不算极端,有异性同学跟我讲话,她会心生不快似的讽刺几句,吵嘴也是常事。直至后来隔壁女孩想给我传情书,竟被她带人堵在厕所里扇耳光。
这件事闹得很大,几方家长都叫到学校去了。一间窄窄的校长办公室,加了几隻方凳,我母亲坐在两个更强势的女人中间,显得十分无助。先是两个女生的家长相互指责,话题流转,竟把我推上靶子的中心。
李芳年的妈妈斜眼盯着我,大声问老师,「有没有可能是这男生故意招惹两个女孩子,让她们產生误会了呢?」
班主任说:「他只是个刚转来的学生,应该」
李芳年的妈妈打断老师,武断地说,「我的女儿不可能无缘无故打人,老师,您也知道我女儿一直是班长,学习委员,怎么可能主动去欺负别的同学?」
「我们阿靖也不会教人去打架的呀。」我母亲急着说,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来。
「一直转学,学习还这么差,您这么说我们能信吗?」李芳年的妈妈反问道。
母亲的脸变得通红,很快又惨白下去,她嘴里说着「不会的,我们阿靖不是这样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辩解下去。
我看了一眼李芳年,她抿着嘴,目视前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又转头去看那个递情书的女孩,她抽噎着,脸埋在她妈妈的手臂上,也没抬头看我一眼。
李芳年的妈妈还在念念叨叨,对校长说着她臆想的理论。我个性软弱,虽然委屈,一句反驳的话也没能讲出来,只期望着我母亲能大声把事实告诉她们。
母亲只教我善良,谦让,但是从没教过我人生还需要争辩和兇狠。最后的结果是,我和李芳年一起被记了过,向那位被打的女生道歉。
惩罚告一段落之后,李芳年像是变了一个人,找老师换了座位,离我远远的,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成熟较晚,也没看过什么啟蒙的剧集和电影,有时候电视上播放男与女的热烈镜头,母亲就悄然转台,当做那段情节根本不存在。
那个年纪,我只是朦胧知道,男女之间有些事会发生,但对那些牵手、亲吻的镜头一知半解。
经过那个风波,我突然意识到感情里的嫉妒、爱、恨都发生地那么疾速,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它们就风捲残云似的结束了。
而结束之后留下的就只有痛苦而已。
我和周远洋简单聊过这件事。
那是刚搬去大舅家两个月的时候,晚自习放了学,接近十一点鐘,其他人都睡了,胡妈留了点宵夜,我拿去温热。
周远洋从自己的书包里摸出一隻淡蓝色的信封,他反过来看了两眼,直接把信攥成皱巴巴的一团,丢进了厨房的垃圾桶。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他丢掉女生偷偷塞给他的东西。
「有人给你写情书了啊。」
「无聊。」
「你都不看看是谁写的吗?」
「知道又能怎么样,我又不会回覆。」周远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