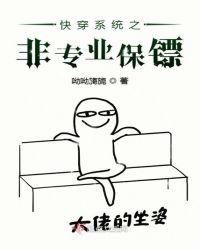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手足+番外 > 第130章(第1页)
第130章(第1页)
除了刚才开宴之前讲话的几位大头头,这一桌的人大都很陌生,他们十之八九肩膀上都扛着至少一颗金星,朱海峰在里面的军衔是最低,年纪是最轻。
当然,三个年轻人的到来刷新了这个记录,不过上尉军官把他们带到之后立刻敬礼告辞,单尔信和郝靓便成了唯二的两个异类。尤其是郝靓,她还是唯一的女性。
本以为两人站着敬完酒,听完训话就能完事,可整个演习的指挥官中将参谋长刘沙居然大手一挥,示意勤务兵给两人加了座位。
这下,连单尔信也不淡定了,外人或许看不出来,郝靓却是从他脸颊的轻轻鼓起看出他正默默地折磨自己的咬合肌。
刘沙五十多岁,面相斯文,颇有儒将之风,只是眼神却极具穿透力,即使微微笑着的时候也让在他面前的人有被看穿的感觉,和他目光接触的时候,郝靓和单尔信下意识地都调整了下坐姿。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为了‘sz’号,为了n舰队一百多名官兵的生命安全,我敬你们两人一杯。”刘沙说着,竟然站起来举起酒杯。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如果说刚才还是心里还是在打鼓的话,这下堪比重锤打击了,尤其是郝靓,想到那个黑瘦的李闽即将面对军事法庭的制裁,想到他家里的病妻幼子,一个没忍住,差点下意识地去否认。
借着桌布的遮挡,单尔信一下子握住她的手,紧紧握了一下才松开,然后两人迅速站起来接受领导的敬酒。却没有说什么,或者是,他们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没有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之前。
刘沙的笑意加深一些,他看向郝靓:“临危而不惧,怀才而不傲,不为人知亦不恚,可谓剑胆琴心,颇有古君子之风,郝翻译是哪里人?”
郝靓心里纠结,面上却依然平静,也微笑道:“祖籍江南c城。”
“哦?c城郝家?你认识郝明堂郝老先生吗?”刘沙的问话带些微微的惊讶。
郝靓面色一端,垂首微微示意:“是家祖父。”
刘沙的惊讶更甚,甚至有些惊喜的意味。军区司令员早在开场的讲话之后就因为公务离开了,在座刘沙职位最高,因此说话就比较随意,他招呼着满桌的人:“你们这些大老粗们,今天可有幸见到了一个真正的书香门第大家闺秀,江南郝家的嫡脉啊,到现在二十几世了?”
承载着近乎全桌人的目光,还有那么多的将军大佬在列,郝靓依然平静且恭顺地回答:“目前家长是我大伯父,二十四世了。”她所关心的,还是情况怎么会传出来,舰长不是已经下令禁言了吗?
刘沙不胜唏嘘:“还是在读书的时候有幸见过郝老先生一面,铮铮风骨,名士风流,至今难忘。说到老派名士,现在大都只能去海外寻觅踪迹,郝老先生是内地硕果仅存的了。”
人家夸她爷爷,她自然要继续淡定地听着,这么久没见,也确实想他老人家了。不过爷爷在她眼里可不是什么名士,他的胡子被她揪掉的,没有一百根也有八十,爷爷样样出色,唯独是个臭棋篓子,不仅下不过奶奶和父亲郝敬,连郝靓在13岁之后都能赢他,他不仅棋艺差,棋品也不怎么样,经常被眼明手快的郝靓捉住作弊,然后“惩罚”。
想到爷爷奶奶,郝靓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略略放松,面上带了一丝微笑出来。
刘沙和众人的关注焦点都在郝靓身上,倒显得单尔信像是个陪同前来的摆设,不过他本人似乎毫不介意,一直正襟危坐,神色平和。
许久之后刘沙才顾得上他,语气就随意多了:“这是单家二小子,季将军的外孙,可够出息的。听说还是当年b市的青少年游泳冠军,在军校的时候我们n舰队的蛙人大队专门派人跑了一趟想去招他入队,人家不来,还以为他是怕吃苦,结果进了a大队,你们说这不是捣乱嘛!”
在座的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物,刘沙透露的讯息已经足够多,再看向单尔信的目光也变了性质。
一顿饭吃下来,快要结束的时候,郝靓还是没问出李闽的事情到底如何,心里就有些着急,可贸然询问却又欠缺些“天然呆”的胆量,正犹豫的时候,单尔信开口了:“这次跟着sz号参加演习,收获颇多,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教。”
刘沙微笑,说出的话却让人笑不出来:“sz号在编的全体官兵,这次出航的以及没出航的,正在基地进行封闭式学习,你们走之前是见不到了,不过单小子,你考不考虑调来我们n舰队?”
果然还是出事了!而且没想到这么大的动静,难怪这场宴席到现在也没见到“sz”号的熟人呢,原来都被关起来再教育了!郝靓再也维持不住面上的平静,眼睛里显现出茫然无措,难道,是自己的多事害了他们?那个脾气火爆的舰长以及温和有礼的指导员,还有那一船的官兵。
刘沙继续说着催人心肝的话:“sz号作为重中之重,船上装有多处实时拍摄像头。”
单尔信闻言额头青筋暴起,他嘶哑的声音经过压抑之后更加低沉:“既然如此,那么多的遥控炸弹和炸药是怎么带上船去的?”
刘沙还是微笑,笑而不语,老狐狸般微微眯起眼睛,似乎在问:你说呢?
这下郝靓的脸色也变了,假的,居然是假的!原来一切竟然是演习中的演习,郝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想也不想便问道:“那舰长和指导员,他们知道吗?还有李闽,他……”李闽当时的绝望和疯狂,以及疯狂褪去之后的茫然和悲哀,如果都是演戏,那郝靓坚决支持他当选金马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