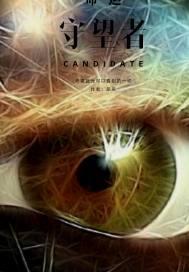墨澜小说>孟大小姐 > 第103章(第2页)
第103章(第2页)
钟漱石喉头紧绷着,很细微的咽动,看着她朝自己走过来。
他蹙了下眉,一句要做什么还没有问出口,呼吸已满是那股清雅的芙蕖香。
孟葭用力垫起脚,她主动吻上他,技法生疏得要命。
钟漱石揽住她的腰,将她抱起来,孟葭顺杆而上,两条腿缠在了他腰间。
他把她放到台上,柔黄的光影里,她闭了眼,全凭着感觉舔舐他的唇。因为不得其要,反而生出杂乱的痒。
钟漱石折过她的后脑,微微张开嘴,反制住她的唇舌,难耐地搅弄着,吻出一阵密密的水声。
他的吻压到她下颌上,又吮弄住耳垂,嗓音很哑,“帮我摘一下眼镜。”
孟葭睁开眼,一双眸子水润润的,拈住镜腿取了下来。
她也去吻他的侧脸,湿湿的嘴唇,碰到他的耳软骨,“钟先生,我现在就可以。”
钟漱石浑身上下的燥热,一下子屏息住,他气息略微不平的,“大晚上的,就这么考验老同志啊?”
原来吻他是为了这个,她吻他,含了近乎献祭的意味。
孟葭嗤的一声,笑了出来,歪倒在他的肩头,“我是说认真的。”
钟漱石双手撑着中岛台,孟葭就坐在上边,他说,“那你可想好了。”
她强撑着一口气,点了点头。
孟葭很清楚,自己迟迟不肯走进这段,欲盖弥彰的爱里的原因。
她太害怕,仅仅是偶尔的见面,控制不住的拥抱,沙发上的失控,就已经让人心潮起伏。偶尔走在路上,冷不丁想起来,心跳得厉害,脸上烧出一片通红。
倘若日日西窗剪烛的话,孟葭不敢想,会蜕化、演变成什么样子。
人人都在撒鸡汤,说凡事有个难忘的过程就好了,不要太在意结果。
可这天底下,谁不是为一个结果活着的?注定两败俱伤的事,又何必要开始呢?
但老天爷偏和她作对,就不让人好过,非要送她到繁华地里,绮丽堂中,真正去历一回醉生梦死,看她有没有本事,能不能度这个劫。
孟葭藏在背后的手,悄然攥紧了,“我明年要出国读书,你不可以限制我。”
“当然。”
钟漱石失笑,他把她当成什么老封建,不许人念书的?
孟葭又停了下来,小脑袋瓜子里,像在计算着数据庞大的公式,最后说,“两年,两年我们就分手。”
这是她的极限了。到那个时候,谭家人的怒气不再那么盛,她也临近毕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