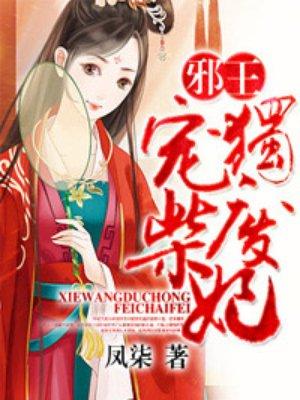墨澜小说>你怎么知道!? > 第14章(第3页)
第14章(第3页)
脑子里乱麻一团。
似乎和一个镇子的利益比起来,和一个镇子上有血有肉的老弱病残的生活比起来,傅今一个人的牺牲,或者说傅行畏一家人的牺牲,实在算不得什么。
却又实在太有必要。
总有人需要牺牲掉什么,才能为群体换来希望与利益。
是这样,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狼群总需要头狼……
安逸很明白,明白得心里泛酸。
可是脑子里更深处的地方,清清楚楚地横亘着一个念头——凭什么?
傅今才回来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和这个镇子能有多深的羁绊?他和傅行畏之间能有多深的感情?能让一个十八岁都没满的少年,几乎算是放弃前尘,为了他们,活得风里来雨里去,活得危机四伏。
安逸心里纷杂烦扰的念头,风暴似的刮着。
不对,不对。
他太了解他哥。
这人是能为一两滴泪水就心软的家伙,看起来凶神恶煞,其实比谁都温柔,都懂得照顾周遭人的心情。
安逸懂得,看到镇上老人浑浊的泪,看到子女尖叫丑恶的嘴脸,看到生身父亲奔波劳碌的日子。
傅今不可能不搭把手。
可傅今,今年也不过只比安逸大了一岁,十六岁的少年。
十六岁,若在青市,傅今该是多么恣意潇洒,随心所欲。
这样想着,安逸一腔发泄不了的愁绪,莫名就找到了倾泻口。
对哦,要不是他爹同意傅今搬走,哪儿来这么多事。
他这会儿宁愿当个鹌鹑,宁愿傅今从来没来过这里,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姓甚名谁。
至少这样,他还可以继续做安家的少爷,还可以在安家的庇佑下,活成少年的模样。
安逸:嗯,都怪贺晓峰。
这么没用,都瞒了十几年了就不能继续瞒着?咋就让他哥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了呢?没用的老男人。
远在荷兰谈生意的贺晓峰突然打了个喷嚏,抬头看了眼荷兰明媚的阳光,疑惑地拿手帕擦了擦鼻子。
至于他牵挂着的小兔崽子,正在钰市十三中按部就班地上课。
学校,课堂,环境,同学。
其实对安逸的成绩影响不大。
倒是傅今的存在对安逸影响能大点。
傅今这人,自从他爸受伤后请过一周假,后面几乎就没怎么逃过课了。
虽然上课还是一副“讲台上的全都欠我钱”的样子,但好歹人在了,心在不在,就只能另说。
一点一点来吧,总不能真要求他一口吃成大胖子。
月考的时候,安逸由于是转校生,毫无悬念地被排在了全校最后的一个考场。
安逸本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倒是周文志和胡莹莹咋咋呼呼的,看到考场座次表过后就围到了安逸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