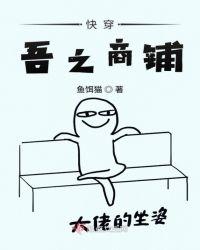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死去的白月光为何秘密满身 > 第102章(第1页)
第102章(第1页)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人的话匣子打开,越来越熟稔。裴长虹看着钟幸不住叹息:“你怎么就在付无疾手下做事呢?”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裴长虹又闷下一口酒。
钟幸原本夹了一筷子白汤清笋,细细咀嚼着。听着裴长虹的话将嘴里的食物咽下去,故意道:“裴将军这话可就说笑了,付大人可是在下伯乐,若无付大人想必单以在下自己短短七八年哪里能够坐到现在的位置?如若没有现在的地位和眼界,哪里有资格和将军见上呢?”
“这倒也是。”裴长虹觉得钟幸的话很有几分道理,不过想到钟幸在刚才谈话中说出的东西,还是忍不住挖人,“按着钟大人的话来看,前程都是自己挣来的。那么钟大人有没有想法另择他人?付无疾跟着的那位……”
裴长虹顿了顿,接着若无其事道:“钟大人也知道贺家的事,那么高堂之上哪里会有青天白日?”不过是同流合污。不对,裴长虹纠正自己的想法,平治帝该是主谋才对。
钟幸在桌下按了按谢微白的手安慰他,然后笑着接:“如今四境乱象肆起,谁也说不准。”
裴长虹听到谢微白的话,沉默了会儿,闷头吃了口酒才继续说:“……不该如此。谁的业报就该落到谁自己身上去,哪里有叫天下百姓替他受业报的。”
钟幸没接话,裴长虹知道他的意思,但在心里还是有些疙瘩。他掀起眼转而看向谢微白:“谢二,你觉着如何?”
谢微白停下给碗中鱼肉挑刺的动作,将挑干净刺的鱼肉放到一旁的小碟上后,筷著摆在碗旁后说:“将军希望我如何觉得?”
裴长虹笑道:“怎么又问回我了,谢二,该是我问你啊。”
谢微白:“我与将军想法自然一样。”
裴长虹眼中笑意不减,他放下手里的酒杯,叹气摇头:“可要是走上这一条路,我就要重新去燕州了。”他的声音里满是遗憾,眼中是渴望也是害怕,“我已经二十一年没有见过燕州了。”
是期待,也是害怕。他知道那片土地上有自己要守护的百姓,那片土地上布满鲜血,自己痛苦的回忆。他也知道那片土地也在努力活着,可是……可是他在十六岁的时候
钟幸笑道:“那可真是再好不过,我两叨扰将军多时,还望将军海涵。”
裴长虹摆摆手:“哪里的事。”说着,他又用复杂的眼神看向钟幸,“幸好你没有跟跟付无疾同流合污当皇帝的走狗,不然……”不然除去付推再加上他一个钟幸,平治帝想要将贺家除去再将自己摘出来恐怕要比现在快得多,或者说现在已经可以将自己摘出来了。
虽然知道裴长虹不知道付推在平治帝面前演戏,但是作为知道内幕的人,在听到别人说付推是平治帝走狗的时候内心还是会很复杂。就是不知道裴将军在知道付推其实也在想办法拉下平治帝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不过这事恐怕自己看不见了。
谢微白将右手旁的小碗往钟幸那边递了,半倾着身子,垂下来的长发遮住了他的动作。他问道:“将军中意哪位皇子呢?”
是了,平治帝若死了,定然是要有皇子继位的。裴长虹的手指摩挲着酒杯,看着有些纠结,没有回答谢微白。
谢微白点破裴长虹纠结的点:“想来裴将军该是中意二皇子的。毕竟这样知人善任、礼贤下士、聪慧过人又对黎民百姓感同身受的宗室子弟,除去他别无他人。”
“……是啊。”裴长虹叹息,“这样一个天生明君,为什么他外家是姓贺呢?”
就是因为中意殷岂才让裴长虹这样痛苦。如同谢微白所说,殷岂自小不因自己出身而对他人无礼,哪怕是宫中地位最底下的宫人他都能以礼相待。少年时期就能够为受了冤屈的大臣向平治帝上言,请求赦免。那时候赵家女入宫,贺皇后失了圣心,也或者说借着赵家女的原因,平治帝终于撕开了多年的遮羞布。
大臣因为早年的一些言论早就不被平治帝待见,那一次的事正是平治帝发泄的口子。最后那位大臣被调离定都,而殷岂则是被平治帝以“目无尊上”的缘由,在南书房外罚跪两个时辰,而后还有一个月的禁足。
哪怕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殷岂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本心。多么难得的一个皇子……裴长虹不甘地重重叹了口气,可他外家偏偏就是贺家!
钟幸终于将碗中的鱼肉细细吃完了,放下了筷子。碗筷接触发出了轻微的声响,谢微白直接偏头看向他的碗,用口型询问:还要吗?
钟幸浅笑着摇了摇头,然后扣了扣桌子,这下引来了裴长虹的注视。他正了正脸色:“贺家通敌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哪怕二皇子多么优秀,凭着他的外家他就是不堪就任大统。”哪怕那些事情和他半点关系都挨不上,但是他身上无论如何还是流着一半贺家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