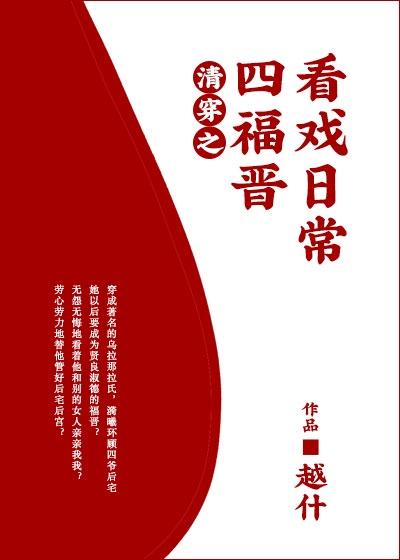墨澜小说>艳一枝春 > 第 11 章(第2页)
第 11 章(第2页)
“没人告诉过你,眼泪流得太多,就不值钱了?”
陆行渊居高望她,面容总教人半分都瞧不出深浅,只宽大的手掌牵袖擦她哭花的脸,不算轻却也并不重,略显粗糙的掌心,说不清有意无意地,拂过她被捏得嘟起的唇瓣。
沈容音眨了眨残留泪渍的长睫,灯下看他幽深眼底,她不动声色微抿起了红唇。
可他说的那是什么话,听了那么多,就只感到这份不值钱?
他如今是铁石做的心肠吗?
陆行渊觑得见那悄悄避让的小动作,眸底漾出几分轻笑,并不动声色,指尖沾染到女人眼尾的泪水,他递到唇边尝了尝,酸涩的、带着点苦味,可见有人是真委屈。
她都这么委屈了,偷东西那遭就算了。
“我的玉环呢?”
沈容音的心思,正因为他那尝眼泪的动作,略微有点飘忽了。
听那话回过神,脸颊还在他手里,她不大自然地低垂着眼,抿抿唇说:“那是我的。”
他显然从始至终知道东西是她拿走的,沈容音再狡辩多余,她嗓音低低的,但不仅反驳他,还要质问他,“你如今既然不肯承认你是宗云谏,还带着我送的东西做什么呢?”
沈容音掀起长睫直勾勾盯着他看。
那男人倏忽倒是弯唇笑了,唇边弧度颇为不讲道理、且理直气壮。
“我何时不承认过?”
他耍无赖!
宗云谏怎么会这样对她!
沈容音满心不想认他,揪着两弯细眉抗议,陆行渊瞧那眼神儿,曲指磕在她脑门儿上。
“明日申时前将玉环物归原主,晚一时半刻,按偷盗罪论处,在你头上烙个贼字示众。”
如花似玉的一张脸,顶着个贼字,想想还挺有看头的。
沈容音双眼怒瞪着他,男人说完手劲儿略松,她忙使劲儿,扭头脱离了他的掌控。
脑门儿还有点痛。
陆行渊似是而非地笑了声,转身出门,吩咐婢女给她送
衣裳进来,沈容音听着那话,才后知后觉自己穿得有点少,可总归如今在那男人眼里,她身上早就只剩件心衣亵裤了!
穿戴整齐,沈容音出去又碰见周管事,人还记挂着问:姑娘要不要吃点东西?
气都要气饱了,还吃什么饭!
沈容音望了眼南边书房,通明的窗户中透出个修长身影,沉沉呼出好大一口气。
她摇头道声谢走得头也不回。
周管事瞧着那背影摇头笑,这便招呼了两个婢女,进寝阁里去更换熏香被衾。
沈姑娘在屋里睡了两夜,相爷就在书房将就了两夜,其实何必呢,相府到处空荡荡,除了孔雀苑那巴掌大的地方热闹过头,其他四处院子都空置着。
可相爷回来就将人放那里了,不仅放,连熏香都换了香甜的鹅梨香。
周管事心下暗忖,不将相爷当相爷看,只当个寻常男人看时,那心思也挺好琢磨的嘛!
正在廊下瞧着无月夜空出神,书房里忽地唤了声,婢女进去片刻出来让备马车。
相爷这么晚还要出门?
相府的马车漏夜而出,行出街巷后小半个时辰,停在了京畿府衙门前。
陆相爷深夜驾临,值守官员诚惶诚恐,忙亲自提灯在前带下地牢。
衙役点亮刑房灯火,光线摇曳扩散开来。
陆行渊踩着布满血污的地砖,提步至椅中落座,看了眼刑房正对的那间牢房。
里头干草堆里盘膝闭目端坐着的,正是昔日贵不可言的临安侯,哪怕如今落魄了,穿着身破败脏污的囚服,沈侯爷也仍旧一派威严,半分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
当真好个萧家的肱股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