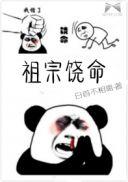墨澜小说>公公与我鬼怪抓抓抓 > 第145章 案29陈植之巧助山石归2结案(第1页)
第145章 案29陈植之巧助山石归2结案(第1页)
“阿青你听话。”陈植之喊住了她的马的名字,不管她在马上怎么用力,人就给定住了。白焆当即回头看陈植之,陈植之却不看她,而是望向钟准说:“阿准,你也算了。”
讲完,他拍了下马肚子,过去抱拳,行礼后道:“是我们不对,阻了几位官爷的道路,还望海涵,莫因我们误了官爷的事才好。”
他讲完,抬头看向方才顶撞了钟准又骂了白焆之人,只见那人睁着一双吊梢大眼,凶狠地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目光在他侧坐马的姿态和被雨水弄得更加埋汰的袄子上停留半秒后,那人收了视线回去,嘟囔一句:“几个乞丐……”便扬鞭,策马带队而去。
见他走了,陈植之说“阿青听焆儿话。”那白焆身下的大青马才重新听话,三人骑着马往前,走了好一会都没人说话,又是好一会,钟准忽然看了看自己,再看了看陈植之,失笑道:“我们真的好像乞丐。”
“唉……”陈植之点头,无奈讲:“像乞丐好,像乞丐命长,安全。”
白焆其实一肚子火,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发才没说。此时听到陈植之说“命长”“安全”反倒是自己好像不懂事了,憋了火也没法说。
她不高兴,就拿鞭子打了马讲:“跑起来!”说罢就自己跑了起来。
见她跑了,钟准也没办法只能骑马去追,陈植之跟在后面跑了一会,眼见两人都要不见了,无奈之下只能改了坐姿,这也扬鞭追了过去。
白焆跑太快,她马又是最好的,陈植之跟着跑了一个多小时,才总算在一个上坡地又看到了白焆和钟准二人。
准确说是,先看到了马,才看到了人。
陈植之一路过去,路边看到了两匹马悠哉悠哉边走边吃草,但马上没有人,他一下心脏病都要出来了,再看钟准那匹白底黑花的小梅花的马鞍上还有他说过好重要的砚台。实在是不知他是心太大,还是胆够肥,他人若是还活着,能让马这样?
差一点就要给吓死了,还好他拉了马过来,没跑多远就看到了白焆和钟准。
二人一个背着剑,一个背着娃和剑,居然在帮人家推车。
“你们俩倒是古道热肠啊!”
陈植之牵着马追过去,有些生气讲。没想白焆埋头帮人忙,居然闷声回了他一句:“谢谢表扬。”
我是在表扬你吗?
陈植之都想骂人了,但转念看他俩帮忙的这堆人,打着旗子,似是镖局模样,一个四马一牛的大铁车,车上……
放着一块最少有三丈长宽的大石头。
此时遇到上坡路,别说人,马都给拉得在前方嘶鸣,此时铁车两边后方,加上白焆和钟准,十七个人弃用力,才保住那车没直接往后滚下去。
情况十分危机,若没有白焆和钟准突然出现,古道热肠,这些人说不定已经人仰马翻,到山下去了。
陈植之见状,不敢骂儿媳了。只是他不骂白焆,白焆居然骂他了,讲:“没见着缺人手吗?公公你给搭把手!”
“我搭把手?”陈植之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会相信自己这根废柴。
搭把手是肯定不会搭把手的,方才一路狂奔,陈植之腿都痛了,下马就瘫痪,怎么好搭把手?
但他是个男的……
我恨我是个男的!
愤恨之际,忽然,陈植之瞧见那石头上隐约有字,他策马往前一点,看到果然是石头上有字,不知是何人手笔,碗口大两个刻字,曰:“庆云”。原本刷了红漆,但此时红漆已经退了。
再看这石头,给镖局押运,倒不是普通石头,看皮色应该是一块天然的白玉,不说玉质如何,单说天然生成这么一块,还全身带着皮,非是山上开采,而是不知多少万年前便脱落开,经过了雨雪和冰川的冲刷才得了这一身的好皮色。
单就这一身天然皮色,这大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