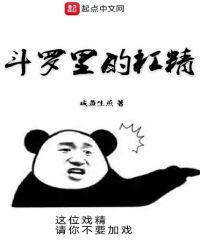墨澜小说>娇软表姑娘 > 第167章(第1页)
第167章(第1页)
“待我吃完鹿血羹就去。”
夜空像被泼了浓墨,一丝光亮都难以被折射,就连天边的疏星也黯淡无光。
前院的空阔之地,四周都掌上?灯,暖黄的烛火似有温度,但?谢璨见不到,也感受不到温意。
二十四盏灯尽数点燃,亮得如同白昼,谢澜坐在廊下的红木扶手交椅,旁边端坐的是一身素衣的沈珏。
芸娘跪在中央,肩上?的包袱被摊开来扔在地上?,她却毫不在意,所有的注意都被左侧的锦衣公子吸引。
谢璨失明后,需要有人做自己的眼睛,低首的长?随快速地瞟一眼,附耳低声?描述。
听?到沈珏也在场,他颓软的身形登时?绷紧如筝弦。
未几,一个嘴里被塞了抹布,支支吾吾的男子被押了上?来,强行压跪在芸娘右侧,他一见到芸娘,瞪着两只耗子眼,嘴里的支吾变得更大声?。
柳氏是最后一个来的,纵使深夜,她亦是一副妆容完美的模样,见到地上?跪着的芸娘,心尖蹦了蹦,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澜哥儿?深更半夜是作何?阵仗呢?”
谢澜神色淡漠地直视前方,不知在看什么,没有说话。
她觉得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脱离自己的掌控,柳氏自说自话道:“既如此,我就先回澧兰堂入寝了。”
他终于开口?,声?线犹如雪沫落在刀锋,“不急于一时?。”
当家的是谢澜,她只不过是个没有一儿?半女的继母,掌家权也被剥夺。柳氏深呼吸,平复好心绪,周边没有给她准备椅子,只好悻悻地站在原地。
“人都到齐了便开始吧。”
谢澜令下,邓唯手执一尾长?鞭甩开,鞭子打在地砖上?发出“啪”的脆响。
芸娘不禁身心皆颤。
“说,半夜三更你要收拾细软是要做什么?”
谢澜单单坐在上?首,血雨淋漓洗礼出的威压就让人喘不过气,芸娘几乎承受不住地趴在地面,牙齿死死咬住下唇。
她不说,谢澜自有办法。
“啪”地一下,芸娘右侧的李荣挨了一鞭子,他痛得目眦欲裂,叫声?被嘴里的抹布堵住叫都叫不出来。
“还不肯说是么?”
又是几鞭子落下,如若不是塞着布团,他定会痛得咬掉自己的舌头。不一会儿?,后背的衣衫被抽成布条,露出稀烂的血肉。
“唔……唔唔唔!”李荣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芸娘,他的娘当真如此狠心。
“我、我说!我说就是了……”芸娘连自称都忘掉,颤巍巍道,“我鬼迷心窍,偷了夫人的首饰,想要逃走。”
摊开的包袱里俨然躺着几对缠枝宝相花翡翠手镯与金叶子、碎银等值钱物什。
芸娘心里的第?一道防线破了,谢澜眉心蹙了蹙,“二十二年前你在松柏树下埋了什么?”